——《中国当代教育实验史》读后
近些年教育理论著作出版了不少,但上乘之作似乎不多。熊明安、喻本伐二先生主编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中国当代教育实验史》新近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结构完整、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评价公允的优秀教育理论著作。
科学发明有赖于科学实验,教育理论的发明亦有赖于教育实验。我国过去教育理论发展甚慢,与长期以来不重视教育实验、不重视对教育实验经验教训的总结甚有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工作者通过教育实验对教育理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教育实验更是开展得如火如荼。有鉴于此,总结近50年来教育实验的经验或教训,对于教育理论工作者将是甚有价值的。《中国当代教育实验史》试图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该书对新中国成立到2000年这整整半个世纪间的教育实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时序清晰,背景相对广阔,所以视其为一部新中国教育史,似不为过。最初的 “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实验,是从河南解放后的1948年开始进行;最后一个 “集群式模块课程”实验,开始于1990年,到2000年仍在拓展中。该书所集中研讨的实验共有33个,这当然只是管中窥豹;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教育实验蓬勃发展,是否有太多的遗漏?其实不然,《中国当代教育实验史》对相关的教育实验进行了归类研究,故堪称“当代中国教育实验大百科”。具体而言,每一个实验的研究结构也相对完整,均有实验由来、实施内容及原则、实验步骤举措、实验的影响及评价,因而既能够对实验的来龙去脉看得分明,又能对其横向要素和操作要领做出精要介绍。唯其如此,这项研究才可能既有“景深性”,又有“广角性”并可能更好地发挥它应有的社会效益。
《中国当代教育实验史》做了相对深入的挖掘,觅得不少珍稀“矿藏”,丰富了教育实验史研究的内容。如“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的办学模式实验,前溯工农教育和干部教育的历史渊源,联系贯彻“教育改造”方针的现实需求,又搜寻到相关的“苏联经验”,将“工农速成中学”办学模式实验的由来阐述得较为清晰。再如“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实验,该章对“历史缘由”进行了深入剖析,从东方到西方,从苏联1918年《统一劳动学校规程》到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再到中央苏区的“劳动小学”和毛泽东提出的“四个在于”教育总方针,这种研究内容的丰富性,自然显示了研究者的功力。
研究资料翔实,是《中国当代教育实验史》的又一特色。该书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还有其时、其地、其人的照片,从而大大提高了该书的信度。另一方面,该书也并非全凭史料说话,许多论证材料取自研究者的亲身经历,这种切身体验似乎有着更强的说服力。从这里,可给治中国当代教育史,乃至治中国当代史的学者以某些启示:治史不能仅仅从政策、制度、法规出发,还赋予其潜隐的、鲜活的精神。
对中国当代的教育实验评价是否公允,是衡量课题研究成功与否的关键之一。要做到这一点甚难,因为当事人多数健在,他们对于实验评价可能会持有异议,甚至可能会挑剔,因而对于批评或批判难以着墨。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当代教育实验史》的分寸把握相对合理。如“工农速成中学”办学模式实验的评价,说此举由革命战争“速胜论”派生出“速成论”;“文化知识的系统学习,不宜等同于政治觉悟的突击性提高”。虽然有些人从工农速成中学毕业考上了大学,后来也干出了一些成绩,但“那些广为宣传的成功个案,也因未能接受系统知识质量的客观检测而有所逊色”。这种评价击中了这一实验理论上的要害。又如对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教劳结合”办学模式实验,该书认为,这种实验“不可避免地具有盲目性、随意性和模糊性的弊端”,“不可过高地估定它的实验价值”。而对“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实验,该书提出了四大问题:一是实验性不强;二是“奉命实验”;三是过分看重实验宣传的意义;四是教学组织形式、课程、教材和教法未能规范等问题。对于全国各地风靡一时的“农村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中国当代教育实验史》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很多实验美其名曰“综合性实验”、“整体性实验”,实际上还是单项实验,仍然是“局限于教育内部”的实验。该书还指出:“我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要取得实效,显然不是‘在教育而言教育’所能取得成功的。如果还是单纯从农村教育的改革入手,以教育论教育,那么依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该书还将20世纪末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与20世纪30年代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人所从事的乡村教育实验进行了比较,得出了:虽然“实验条件已得到很大改善”,但“从事实验者矢志不渝的奉献精神却似乎在日渐減退”的结论。这是令人深省的问题,值得教育实验者、教育理论工作者反思。
当然,“金无足赤”。尽管课题研究队伍整体实力较强,但个别研究人员的学术底蕴稍欠,在资料的搜求、观点的确立和论证的严密上均有所不足,致使个别章节出现“软肋现象”。
此外,在选点布章方面,个别实验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也似有值得商榷之处,而20世纪90年代蔚兴的课程和教材实验,尽管有的章节做过论述,也似应有专章甚至大章来进行重点研讨。总的说来,这些只能算是“白璧微瑕”。
1905年,德国教育家梅伊曼和拉伊联手创办了《实验教育学》杂志。此后,“实验教育学”独立的学科地位才日渐明朗,真正意义的“教育实验”方具备理论的灵魂,教育实验史也由此跨入一个崭新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2005年正好是实验教育学的百年华诞。《中国当代教育实验史》的出版,实为对这个“百年华诞”所奉上的厚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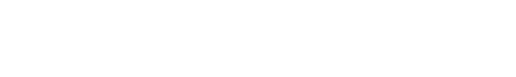
 您现在的位置:
您现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