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是学术造诣深厚的海外学者,为了在市场经济时代充分发挥“诗歌对人的心灵和品质的提升的功用”,使青年人不至于“被一时短浅的功利和物欲所蒙蔽”(《叶嘉莹自选集》第510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出自本书的引文均只标页码),她自1979年起,每年假期自费回国讲授诗词至今。这一带有堂·吉诃德色彩的举动,令人感动和敬仰,更难为可贵的是,她以深厚的诗学修养和极强的感悟力探求诗人之内心,阐发诗人之精微,唤醒了人们对文字之美的回忆。1980年代她的《迦陵论词丛稿》《迦陵论诗丛稿》在内地的出版,给仍在使用以阶级分析方法解读作品的文学史教材的大学中文系带来了一股清新温暖的气息。195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也兴起了“大跃进”,中文系学生以旺盛的革命生产热情参与文学史教材写作,1960年代出版的由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虽然编者大都是名校的名教授,但是,受当时的政治空气影响,掺杂进去了太多的非文学性因素。“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政治解读。直到1979年,郭绍虞先生还在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再版前言中还一再申明:“这部《中国文学批评史》,虽是解放以后印行的,但由于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够,未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提揳全书,因而我只能在《后记》中认为是‘一部资料性的作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类似这样的“检讨”弥漫于各个学科,成为受尽折腾的知识分子所紧紧抓住的一根稻草。
生于燕京旧家的叶嘉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毕业于辅仁大学,为诗词名家顾随先生的入室弟子,后在台湾大学任教15年,又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其学术资源无比丰富且学问事业未遭受人为扭曲,所以,叶先生的论说不仅融会古今、打通中外,而且承继了传统诗论的“妙悟心通”,在诗词批评中融入了个人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感悟,让人在遥远的心灵默契和感动中,有一种循诗词的美学光芒和语言河流溯源而上的冲动。这种抽丝剥茧、慢品细味的阅读方式在当下这个“文化快餐”泛滥的时代已十分罕见。作为山东教育出版社的“汉学名家书系”之一的《叶嘉莹自选集》,收录了叶嘉莹先生的若干篇学术美文,让人感受到诗道的力量、诗美的魅力。
“诗无达诂”,古典诗词为人们提供了广阔的诠释空间,使人们在揣摩体味中感受到诗思的意蕴和趣味。从作品原义出发到若干个衍义,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历程,所谓“读其篇者,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清·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通过深微幽隐到“言外”寻觅所谓的“要眇”之特质是中国的词学传统,在这一点上,与强调读者对文本可能性的拓展的西方阐释学和接受美学是十分相似的。叶嘉莹正是从这一中西方文论的暗合之处,获得了词学批评的真谛。她认为:“词更具有一种幽微要眇引人向更为深远之意蕴去追寻的特质。”(第373页)所以,叶嘉莹在对词的欣赏和评说中,把功夫用在了对意内言外、神不在貌的词家笔法的领悟上面,用精细的审美神经和敏锐的诗学目光去打量和审视语言表层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处情感波动。由于综合运用了文艺学、美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民俗学的方法,叶先生能够掂量出意境的深浅、性情的真伪,她对诗词主题、诗人情怀和艺术意象的阐发都是一种独具匠心的艺术再创造,叶先生认为:“读者在发掘文本中之潜能时,还可以带有一种‘背离原意的创造性’”。(第510页)
回味悠长是古典诗词的一种潜质,经过雕章琢句连缀而成的艳词丽句是一个干瘪的平面,而那些兴象丰富、蕴蓄深邃的诗词则给人以境外有境的空灵感,“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沧浪诗话》)正是这种空灵感使得人们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反复品味那些飘逸的语词,仿佛聆听缭绕的余音。在“深美闳约”与“精艳绝人”之间,叶嘉莹显然更看重后者,铺金列秀、雕绘满眼的诗词往往因为刻意雕饰而失去个性和生命之美,只剩下一张华丽的装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寄托深意的作品才是耐读的,秀而不实的文字错误不在修辞,闳丽的词藻并不必然指向肤浅和庸俗,根本的弊病在于情之不真、意之不纯。清代词家蔡嵩云有言:“文学技术日进,人工遂多于自然矣。”(蔡嵩云:《柯亭词论》)叶嘉莹在评述杜甫的真切文字时,这样写道:“有如此切之深厚之情,所以杜甫写衷心哀痛便可直写到‘叹息肠内热’、‘回首肺肝热’,写哭泣流泪便可直写到‘拭泪沾巾血’、‘啼垂旧血痕’,像这种深情激切之作,又何病于‘显’?又何取于‘隐’?一般人之所以以为写情要用‘隐’为可贵,而以为一用‘显’便不免有死于句下的落实之讥者,主要因为缺少了这一种喷涌洋溢的力量的原故。”(第13页)可见,叶嘉莹的诗词批评是一种洞察诗人用心和诗词“味长”的心灵艺术。她的品评之所以既细腻又大气,而且富有现代气息,是因为她用深沉的人文关怀和个性化的审美目光赋予“兴”、“味”、“神”、“韵”、“逸”等古典美学范畴以更为舒展的阐释空间。将诗人的神遇和超悟转化为可以描述的东西必须要遵循心灵的逻辑,用艺术理性来把握诗词的神化之妙。
叶嘉莹对“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等诗人乡愁的解读之真、之美是无与比拟的。她一眼就看出,“还乡”前面加上一个“莫”字,“正是极端无可奈何之辞。”(第21页)而这种无奈之情又偏偏隐藏在对“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的强颜欢笑之中。叶嘉莹说:“夫人情同于怀土,游子莫不思乡,‘江南’既是异乡,‘游人’原为客旅,何以偏偏却说是该合江南终老?此二句虽是以他人之口道出,可是若不是游子的故乡已经有不能得返的苦衷,异乡之人又何敢尽皆以如此断然之口吻相挽留?”(第20页)通过还乡诗词分析诗人的人生际遇和心灵律动,仿佛切开了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断面,使人们在“味外之旨”、“韵外之致”之中体会到了人类命运的悲苦和追求理想、寻求精神归依之艰难。委曲含蓄之中体现了忧深思远,平易词句间饱含着深沉喟叹。还乡而不得是人类困境的一种象征,思乡之情是人类痛苦的典型表现,人生如梦,时间无情,青春转眼失去,一切都被搁置在途中,只能发出“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的感慨。此种伤感,此种情怀,伴随着人类精神跋涉的全过程。有告别,就有怀念;有孤独,就有慰藉;有奔走,就有梦想。叶嘉莹的诗论是关怀人生、观照现实的。发达的信息技术使得传统诗词相思之苦化为无聊的短信和QQ里的胡言乱语,对时间的焦虑并没有因此而化解。人生苦短的悲情与惆怅是当下这个“娱乐时代”所竭力回避和掩饰的人性现实。所谓“老鼠爱大米”,一切都没有来由,“无厘头”足以解构一切。
钱钟书在《谈艺录·序》中说:“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将忧世情怀融入作品赏析之中,是一种大境界。叶嘉莹没有把诗词批评当作自娱自乐的学术游戏,而是有着鲜明的价值选择。叶嘉莹在《我的诗词道路》前言中强调自己对诗词的评述追求的是“一种心灵与感情的感发之力量”,因为她的诗词道路经历了这样一个转变,即:“有为一己之赏心自娱的评赏,逐渐有了一种为他人的对传承之责任的反思。”可以说,叶嘉莹在浮躁的学风中创造了为人生的学术的典范。与那些热衷于通过制造“秦可卿出身之谜”之类的学术噱头的媒体学者相比,叶嘉莹的治学态度格外令人尊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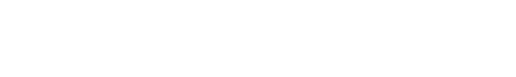
 您现在的位置:
您现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