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飞鸿遗影——钟敬文传》
记得钟敬文先生在世时曾说过大意如下的话:在他身后,如能在他的墓碑上镌刻上“诗人钟敬文”五个字,他就心满意足了,可以安然地闭上眼睛了。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愿和心情。诗人是人类的良心。诗人是心灵的天使。诗人是思想的王者。诗人是读者的偶像。
诚然,他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的十年间,在散文和诗歌创作上取得了卓尔不群、令人艳羡的成就,在后来的一生中,也从未放弃运用散文和诗来记录和表达他的情感和思想,他的《西湖漫拾》和《湖上散记》等清丽婉约的散文,也许比他后来那些既深邃却艰涩的民俗理论拥有更多的读者。但从上世纪20年代末起,他却为在中国建立民俗学的理想和责任所激励,所驱使,几乎放弃了诗人和散文家的梦想,义无返顾地投入了当时还很冷僻的民俗学的研究,走上了一条寂寞而坎坷的羊肠小道。
钟敬文的百年人生中,经历过种种的危难与曲折,但他终于以信念和坚毅、勤奋和执着、宽容和平静相对,一次次从被政治抛掷的“仄径”与“险滩”中站立起来感奋起来,以其思想和智慧,在几乎是荒芜的学苑上为自己筑起了一座学术丰碑。在这座丰碑上镌刻着三个没有任何“高大全”的时髦形容词,却闪耀着持久光芒的桂冠:诗人、散文家、民俗学者。
青年学者安德明君撰写的这部《飞鸿遗影——钟敬文传》(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以娓娓道来的娴熟笔法和信手拈来的丰富资料,记述和再现了他的老师钟敬文的多彩人生和学术生涯,诠释了矗立于学苑之上的这座丰碑背后的故事。读着这部诗人兼学者的传记,不由得令我想起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写的那首流传千古的短诗《纪念碑》里的那些词句:“我为自己树立起了一座非金石的纪念碑,/它和人民款通的路径将不会荒芜,/啊,它高高举起了自己不屈的头,/高过那纪念亚历山大的石柱。”他不计较赞美和诽谤,也不希求桂冠的报偿。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有一批站在时代前面的启蒙思想家,就以反传统的革命文化精神,举起了采集、研究、发扬、利用被封建的圣贤文化和士大夫们所贬抑的神话、歌谣等民间文学乃至民间文化的旗帜,前者如蒋观云、梁启超、黄遵宪等,后者如鲁迅、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胡适、常惠等,一时间形成了一股震惊知识界的文化思潮。继而,茅盾、顾颉刚、董作宾、郑振铎、钟敬文、江绍原也先后参加进来,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加入到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的队伍和名单之中。到40年代及其以后,又有一大批民族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如凌纯声、芮逸夫、闻一多、杨宽,以及在延安的以何其芳、柯仲平、吕骥等参加进来,为创立和发展我国的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学科携手共进。但在历史的长河中,许多在不同阶段上对民俗学运动起过重大作用的学者和文艺家,或因工作的需要,或因个人的原因,或因政治时局的影响,逐渐转到了其他学术领域中去,而惟独钟敬文一人锲而不舍地在选定的民俗学园地里勤奋耕耘,直至百岁之时告别人世也同时告别讲台。由于种种原因,最主要的是当“右派”的年月里和长期政治歧视中耽误了和蹉跎了岁月,使他没有可能给后人留下大部头的专著(如传记中写到的《女娲考》),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但他审时度势,晚年着力于学术体系的建构和学科后继者——学生的培养,在这两方面所留下的遗产,无疑令我辈赞叹。总观全书,笔者认为,与其说传记所记述和再现的,是一位在荒芜的田园里披荆斩棘奋力拼搏躬耕了一生,且多所建树的学者,毋宁说,写出了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高尚人格及其魅力。
概而言之,中外传记之作,要么是史传,要么是评传,仅此两途,概莫能外;而传记的作者,要么是门生,要么是外人,不出这两类。门生写老师之传记(如《飞鸿遗影》作者安德明写他的老师钟敬文)者,中外历史上并不乏先例,作者对传主生平事业的了解是局外研究者所不及或难及的。安著在其对授业老师生平事业的叙述中,所以能如数家珍,所以能以情动人,所以能体味入微,所以有如父如子般的情怀,盖因他长期在老师的身边,除了听课受业外,还有种种外人不能体验的生活和情感的交流。但这样的作者,也注定了眼界和思想的局限性。我们在安著中,也隐约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作者似还缺乏大家的手笔和气度,即既能充分地展现传主的人格、思想和成就,又表现出作者的评判的立场。在这方面,应该说,容格是一个范例。他在写他的老师弗洛伊德的传记时,就既表现出了他作为学生和事业继承人的优长,又兼备了一个评论家眼光和超越老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素质和学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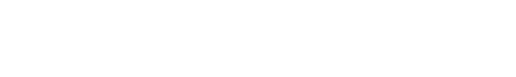
 您现在的位置:
您现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