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守本与开新:阎锡山与山西教育》
李 忠(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
复杂学的出现出于人类对世界的复杂性的观察、体认、思考和研究。在复杂学视域中,复杂性是自然界的基本特点。以20世纪60年代自组织理论、非线性科学为代表,复杂性得到深入研究并引起广泛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力推动下,复杂学研究从传统科学领域拓展到计算机、生物学、人工智能、生命科学、认知科学等广阔领域,进而拓展到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复杂学研究的重要奠基者、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利高津指出,复杂性研究将开创人与自然、科学与人文的新对话;物理学家霍金则认为,21世纪是复杂性科学的世纪。耶鲁大学资深研究员、前国际社会学学会主席沃勒斯坦在《知识的不确定性》一书中,对社会科学中的复杂性进行了深度探索。复杂性引起人们对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重新认识:从存在到演化,从对立到互动,从构成到生成,从寻求确定性到挑战确定性,从理解到应对等等。
复杂学不仅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复杂的,而且单个人也是复杂的。复杂学致力于走出表面、走向深入,走出一维、走向多维,走出局部、走向整体,走出简单、走向复杂。人有多面,只有将人的多个侧面梳理清晰,人的真实面目才能比较清晰、全面地展示出来。这不仅需要多种研究范式的综合、多种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综合应用,而且要求研究者具有多学科的知识背景和多学科的研究视野,甚至需要不同领域学者的合作研究。
阎锡山无疑是这种具有多面性、复杂性的一个典型。大凡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阎锡山是“军阀”、“土皇帝”,盘踞山西数十载,为自身利益不惜牺牲社会公益,为个人荣辱可以不择手段。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或者是革命史范式中的阎锡山肖像。除此之外,阎锡山还有多个侧面。正如申国昌博士在《守本与开新——阎锡山与山西教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中指出的:“他(阎锡山——引者注)学识不丰,却十分崇尚文化教育;他固守传统,却刻意追求开拓创新;他偏居一隅,却热衷于对外文化交流;他行伍起家,却心存教育救国理想;他身为军阀,却酷爱兴教办学实践。”
对教育的认识和实践,是阎锡山复杂多面的一面,也构成解读阎锡山复杂多面的有效渠道。然而,在学术研究领域,关于阎锡山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的研究成果几乎是空白。申国昌博士以阎锡山为研究对象,以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为主线,以大量史料为依据,从多个角度、应用多种方法,对阎锡山这一历史人物条分缕析,不仅对了解阎锡山这一复杂历史人物提供了帮助,而且对了解近代以来山西教育变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山西这个深处内地的省份,到1924,已有1056115名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占到学龄儿童总数的72.2%,男童受义务教育儿童数占男学龄儿童的90%以上,在20世纪上半叶一直居于全国首位,并带动全国义务教育的实施,陶行知曾以“山西是中国义务教育策源地”予以评价。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的统计资料,20世纪30年代,山西拥有省立高校6所,在全国省立高校中名列第一,每百万人中拥有专科以上学生195人,与江苏并列为全国第三。据1922-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调查,山西省13所师范学校的在校学生总数为3442人,居全国第二位,其中女生人数居全国第一位。山西的职业教育与义务教育有并驾齐驱之势,黄炎培于1925年考察后指出,“山西的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差不多已算普及”。到1929年,山西拥有社会教育机构多达12291个,位居全国第一;受教育人数为210386人,位于全国第二位;教职员数17411人,位于全国首位。作为深处内地、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省份,山西一跃而成为世人关注的教育大省,“的确是隋唐之后山西教育史上的第一次”。山西教育成就的获得,与阎锡山这位统治山西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的“大军阀”不无关系,也构成这位“大军阀”的另一面。山西在当时中国的“模范省”以及阎锡山本人的“模范省长”称号,为今天人们认识这位复杂人物提供了证据。历史就是如此有趣,将“军阀”、“模范省长”与“教育救国者”完美地统一于一人之身,而没有遵循任何理论家建构的理论。通过阎锡山透视民国时期山西教育发展变迁,不仅使读者了解到阎锡山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活动,而且了解到民国时期山西教育历史变迁过程。
该书尝试新史学的研究范式,以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为分析工具,综合应用史料分析法、计量史学法、心态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大胆突破原有的研究范式,对教育史学科建设不无意义。
首先,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该书将一个通常被认为是“反面”的历史人物作为研究对象,而且予以正面的分析和评述,反映出作者具有相当的勇气、问题意识和敏锐的洞察力,当然,这些都是建立在翔实的资料和精细的分析基础之上。其次,在研究范式上,该书不再囿于革命史范式——认为“凡是革命的都是正确的,凡是不革命的都是不正确的,越革命越正确”与近代化研究范式——认为“凡是近代的都是好的,凡是非近代的都是不好的,越近代越好”的研究思路,而是以新史学范式与历史史实相结合的方式去考察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第三,在研究方法上,该书突破了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阶级分析和与传统、近代的二分法,而是根据问题的性质和特点将多种方法综合到该问题的有效分析之下。第四,在分析工具上,该书不再坚持单学科的分析,而是将相关学科综合起来,力图全方位地对研究对象做出全面分析。第五,资料的收集和应用上,该书挖掘出诸多以往少见的史料,开辟教育史资料的新源泉;最后,在结论上,由于新资料的挖掘和新工具、新方法的应用,使得该书中出现诸多有说服力的新观点。
《守本与开拓——阎锡山与山西近代教育》这本44万多字的学术专著,突破了以往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简单化、脸谱化的描述和分析,而是将教育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看作一个复杂体,从多个角度和多个侧面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进行全面、整体和深入的把握。同时,该书提出颇具启迪意义的观点。例如:教育正面功能发挥所需要的条件远远多于其负面功能发挥所需要的条件,因此教育的负面作用比其正面作用更容易出现。当教育的正向功能不能出现时,教育的负面功能便粉墨登场了。因此,当乐观者赋予教育重要作用的时候,悲观者却以教育无用论作为回应。阎锡山主要不是一个教育人物,所谓“旁观者清”,阎锡山能够看到并有能力在局部地区解决当时教育中出现的问题。在职业教育实施过程中,由于教育不能适应社会生产生活需要,致使学生“毕业即失业”,出现“害学生、害家庭、害社会”的“三害教育”,针对这种情况,阎锡山利用各种资源和手段积极予以应对。又如,教育从来都不是中性的而有其倾向性或价值取向。作为军阀办教育,除了像人们理解的教育是重要的社会公益性事业之外,还有作为其自身利益的考虑,这种考虑无论从政策的制定、制度的出台上,还是对教育教学内容的选择上,都会有所体现。作者能够利用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工具对此作出深入分析,对于人们认识不同主体参与教育时的态度、立场、强度、范围与效果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认识教育的本质也不无启迪意义。
作为一本具有开拓性的著作,一些问题还值得继续关注。例如,民国时期山西教育发展能否归功于或主要归功于是阎锡山(因为历史不可能是独角戏)?是否有民众基础和民众的积极配合(因为兴办新式教育需要民众的配合,在一些地方由于民众的抵制,出现诸多“毁学”现象)?对阎锡山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活动的过度关注是否会遮蔽对山西教育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其他人物(正如研究者将北大的发展归功于蔡元培,而忽略了对北大同样作出重大贡献的其他校长一样)?等等。这些问题,将可能出现在对山西教育、山西教育历史人物进一步研究过程中。
发表于《教育史研究》2010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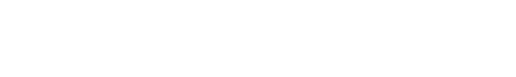
 您现在的位置:
您现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