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月斌
1
我认识融融。去年初冬,大概也是这个时节,我带了两本《张炜论》去请张炜先生签名。才拿出书放到桌上,就听到放在沙发旁边的纸袋发出声响,我侧身想把纸袋扶正,没等伸出手,那纸袋竟腾空而起,噌地一下蹿到书房去了。我没看清是什么,张炜叫了声“融融”,赶紧起身去看。我也跟着进了书房,那纸袋歪落在书桌下,肇事者却不见了。张炜松了口气:它劲儿很大,还好,没勒到脖子。它是第一次见你,还认生,躲起来了,它很好奇,谁带来的东西都要侦察一番。接着又唤了几声融融,让它不要怕,怎么不出来见见客人呢?张炜语气轻柔像是安抚一个孩子,听得出他对融融的宠爱。重新坐下后,张炜说它的好奇心还没满足,很快就会过来。果不其然,话音没落,它就来了,我扭头去看,才发现,那是一只大猫。
那天的话题就没离开融融。它是一只布偶猫,毛色灰白相间,才几个月,体重已有十多斤。虽然刚刚受到惊吓,却一点不失风度,只见它神闲气定,迈着四方步踱过来,在近旁停住了,上下打量着我,像是要辩人面相。我凑过去蹲来,叫它融融,它似乎并不反感,也未乍现热情,只是平和地看了我两眼,便纵身跃至沙发的靠背,在上面俯身平摊,头尾正好搭在两端,显得慵懒而不失高贵。它眯着眼睛,像是若无其事,张炜却说,它在听我们说话,它听得懂,知道在夸它,尽管心里很美,但表现很淡定。这派头完全就是一副宠辱不惊的王者风范啊!看来张炜对融融不止是宠爱,而是崇爱有加了。就是那一天,张炜谈了猫的种种可爱,养猫的种种好处,还说他准备了一台相机,专为融融拍照,以后还要为它写一本好看的书。
2
没想到,仅仅过了半年多,张炜不光把融融写进了小说,还由它打开童年记忆,一口气写了很多小动物,这就是他在新冠疫情肆虐之际创作的《爱的川流不息》。因曾亲眼见过小说的主人公,又经常看到作者发来的炫猫靓照,所以打开这部作品,一眼看到了融融,便倍感亲切,张炜果然写了一个好看的猫故事,写出了一个“大骨骼的人”。张炜是写动物的高手。《古船》中的枣红马,《蘑菇七种》中的宝物,《九月寓言》中的?鲅,《刺猬歌》中黄磷大鳊,《你在高原》中的阿雅,《海边怪物小记》中的狐狸、狍子、小爱物,《我的原野盛宴》中的银狐、老呆宝……几乎所有作品中都少不了迷人的虫鱼鸟兽,不不了神奇古怪的美生灵,登州海角的“它们”早已成为张炜文学谱系中重要一支,简直就是一个生养众多的奇妙王国。《爱的川流不息》无疑给这个国王注入了更多的“爱力”,也让读者看到了令人神往和怜惜的异类世界。
小说里的融融是整个文本的“大骨骼”——它支撑起了故事的主体框架,具有今昔互通,时空并置的叙事功能,因此它是作者半生经历之“爱别离”的回应者,同时也是得其所安的幸存者:它从南方都市空运到北方大城,一生下来就被宠着爱着,寑食无虞,自由自在,几乎不用费力就是一只杰出的猫。但是它的前辈——生活在海边林子里的小獾胡、“花虎”们就没那么幸运了,虽然它们也得到了林中人家的百般呵护,可是总有要命的“不可抗力”,让这些脆弱的小生灵没有活路。有人要把小獾胡打死做一顶狸子皮帽,有人要把小香狗花虎打死“节省粮食”,还有“毒杀三代”的老鼠药把会笑的“小来”毒死。所以小说的主线是融融与我们的长相守,副线则是写小獾胡、“花虎”等小动物和我们的生离死别。
就因为小獾胡身上有野狸子的血统,便被全副武装的“黑熬”盯上了,非要夺其命剥其皮,我们无力保护自家的猫,只好教它逃往外乡。这是“我”的第一个动物朋友,也是“我”经历的第一次远别离。
比起小獾胡来,“花虎”遇到的“不可抗力”更为强大,那是“上边”下达的“打狗令”,“黑熬”们干起“活”来更是有恃无恐,多亏外祖母拼死相救,“花虎”才暂得活命。没办法,只好为它寻求庇护,把它送给比“黑熬”更强悍的人。孰料“花虎”咬断拴绳不知所踪。这是“我”经历的又一次生别离。当地的狗都被“黑煞”赶尽杀绝,“花虎”一去成永别,“我”痛心不已,发誓再也不养小动物了。
第三次,则是眼睁睁看着“小来”中毒身亡的死别离。这是一条差点被人遗弃的狗,“我”看到它的第一眼就“被它所征服”,竟然忘掉了过去的誓言,把它当作宝物带回家里。“小来”在城市长大,“有一副大咧咧的性格,对所有人都没有陌生感,更无提防心。”大概就是一个毫不设防的孩子。然而危险就隐藏于此,当它跟随主人到了半岛乡下,却不知死去的老鼠竟是致命的。归根结底,“小来”死于人类对异类古老的偏见和深深的怨毒。
此外,小说还简略写到了一条叫“宝物”的山东细犬、一只叫“美美”的狸猫、一条强壮的大狗“旺旺”、一只外表凶悍实则温情的花猫“小红孩”,以及鸽子、刺猬、仓鼠、麻雀、红点颏、蝈蝈等一些型体更小的动物朋友。“所有这些朋友,它们有的走失,有的痛别;有的最后不知所终,有的忍痛放回林野;也有的在病危时节,出于动物们特有的巨大自尊,竟然独自逃入了人所不知的角落里,就此消逝。就这样,我们与它们总是非正常分离,经历一场撕扯之痛。”在作者笔下,一次次的“非正常分离”就像沉淀在心底的黑色锈斑,一经回想便会肝肠寸断伤离别,只恨有缘总相隔。
3
“正因为深爱,才要拒绝。”正因有过刻骨铭心的“三别”,“我”才不愿再次永失所爱,不敢重新拥有一只猫。那么融融是怎样进入“我”的生活,又是如何成为小说主角,并让“我”收获了“爱的川流不息”呢?当然取决于人。我们注意到,作者在述说“我”与小动物的悲伤“三别”时,还穿插交代了“我”与父亲的“相见难”。那时的“我”就是缺少父母陪伴的留守儿童。父亲被放逐南山做苦力,常年累月不能回家。母亲也在稍远的园艺场做临时工。平时只有外祖母守着“我”,在林中小屋过活。这样一个聚少离多的家庭,有一次阖家团圆,太阳大概得从西边出来。尤其是困在大山里父亲,有时候好不容易找到机会往家赶,还可能遇上找茬滋事的“黑煞”。所以,“我”的童年岁月,又总是深陷在父子亲人“相见难”的忧愁中。正因相见难,才怕爱别离。正因正常亲情的无以托付,才会对身边的草木生灵爱之愈深。幸好还有外祖母,她懂得让一个孩子与异类交换“心语”。而这颗可与小獾胡、“花虎”们交谈的赤子之心,正是在外祖母慈爱的葆养下慢慢习得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当“我”不再年轻,可以说成了空巢老人,这时,远方的孩子执意送来的“厚礼”,竟是一只唤作融融的猫——它触发了“我”的创伤记忆,激起了沉睡的恐惧感,让“我”禁不住陷入“自己的生活是如此脆弱,个人的能力是如此微小”的自我怀疑中。但是好在,融融是一个自带主角光环的“大骨骼的人”,它一进家门,就成了这个家的新成员,成了令人深爱而无法拒绝的“不可方物”。由此,海边丛林里的外祖母,大山深处的父亲,以及远方的孩子,和“我”一起构成了跨越时空的超验性对话,借助于身有异能的小动物,远方的孩子可以听到外祖母的心语,经历过四次“打狗令”的“我”也可以摆脱对种种“不可抗力”的万般恐惧。所以,这部小说又是四代人共同演绎的“爱的川流不息”,是和“不可方物”的异类们合唱的相濡以沫之歌。
融融从天而降,像是为爱而来的陪伴者、抚慰者,显然代表了“下一代人”对父辈暖心的体贴。不过从他们不多的对话、争论中,又可看出两代人的“动物观”不尽相同。在孩子眼里,融融就是一只为人而生的宠物,所以才会发问:“收养一只宠物真的有那么难?”而在“我”的心目中,融融和小獾胡们一样,都是不可豢养的特异生灵,它们生来自由,只是与人类构成了一种相互驯化、相互陪伴的平等关系。就像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狐狸对小王子所说:“对我来说,你无非是个孩子,和其他成千上万个孩子没有什么区别。你也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无非是只狐狸,和其他成千上万只狐狸没有什么不同。但如果你驯化了我,那我们就会彼此需要。你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我对你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李继宏译《小王子》,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4页)据小狐狸解释,“驯化”就是“创造关系”——有的译本作“建立联系”,在我看来这种驯化关系应该彼此认同,相互信赖,相互给予,互无亏欠。这里的“驯化”(apprivoiser),还有“驯服、驯养、养服、‘跟……处熟’”等多种译法,似乎都不足以传达小狐狸的原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种“驯化”应是一种“养熟”、“养活”,所谓的“养”也不是单方面的饲养、豢养,而是不具依附关系的“互养”:当你养活了一个生命时,对方不也在养活你?正如“我”所感喟的:“自己所能给予它的,比它已经给予的不知要少多少倍。”因此我们注意到,小说里的小动物从小獾胡、花虎、小来到融融,无一不是“我”的朋友,无一不是与我们创造了一种融洽的互动关系。你看小獾胡,本是从野外拣来的小野猫,可是一待长大,外祖母就任由它出门撒野,并未当成私有物品圈在家里。“花虎”的身份更特殊,它真正的主人是看葡萄园的老人,它只是像走亲戚一样在我们家做客。至于小来和融融,虽然“我”身为“主人”,却从不是它们的主子,只相当于它们的监护人,任由它们饱食终日懒洋洋,任由它们独自思索偶忧郁。你会发现,“我”的动物朋友从来不是个人的“宠物”、“玩物”,而是自有一片天地的“这一个”。
4
“创作总根于爱。”《爱的川流不息》即在言说爱的力量。小说里的外祖母这样看待世界:“这里可恨的东西太多了,可爱的也太多了,幸亏是这样,如果光有恨,咱们一家是活不下去的。”又这样表达她的爱恨观:“人的心里,当爱和恨一样多,就算扯平了;当爱比恨多,那就是赚了。”“有爱的人才有无数的粮食。”外祖母朴素的言语堪称了不起的“爱的教育”,她让“我”明白,这世界难免可恨,更不乏可爱,当然首先是让“我”分清二者的界限。“外祖母,爸爸妈妈,壮壮和爷爷,小葡萄园的老人,小獾胡,野兔,鸽子,老广,‘花虎’,美美,旺旺,‘宝物’,刺猬,月亮,大片菊花,马兰草,白茅根和上面飞的大蝴蝶。”——可爱的数不过来。“下杀狗令的人,伏击外祖父的人,‘黑煞’,毒蜘蛛,悍妖,打死许多动物的猎人。”——可恨的屈指可数。用外祖母的话说,“我”是赚大了。
对“我”而言,“可恨”大概只是一小片心理阴影,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亦不足道哉。若是如此,我们看到的《爱的川流不息》很可能就是一道劝善隐恶的佛系鸡汤。张炜显然无意宣教一种肤浅的“好人主义”或“爱的哲学”,他在小说中一面告诉我们,“爱力”也可以是一种强大到无法抵挡的“不可抗力”,同时也在另一面写出了有形无形的悍妖、恶魔造成的伤天害理、祸害人间的“不可抗力”。如果发自本然的“爱力”是阳性的、积极的、有光的,那么与众生有情为敌的“不可抗力”就是“造业”的“恶力”,是阴性的、反动的、黑暗的,为此作者极具象征性地塑造了一个外号叫做“黑煞”的人,把他作为小獾胡、花虎、父亲和整个海边的对立面,写出了“黑煞”之凶残,之恐怖,之避无可避,防不胜防。
对于“黑煞”,民间的迷信说法常常言之凿凿,有人就声称见过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呈人形,没有五官和四肢,会蹦跳着移动,人若大喝一声让它滚开,它就会傻乎乎地溜走。不过也有所谓阳气不旺的人会招黑煞上身,弄得失魂落魄,大病一场,甚至失去性命。小说里外祖母就有类似说法:“什么是‘黑煞’?人走在路上,正走着,只要觉得眼前一阵黑,上不见天下不见地,两脚像踏在半空里,那就是遇见‘黑煞’了!只要遇见了它,也就十有八九活不成了。以前有一个猎人,他就遇见过‘黑煞’,没死,不过在床上躺了半年,身上蜕了一层皮。”虽说“黑煞”只是“迷信”,但从“科学”的角度看,未必不是一种超出我们认知的能量场或暗物质。当然小说只是借用这种迷信之物,极像“黑煞”一样可怕的暴虐之徒。他生得又黑又矮,身上没长肉,全是筋,嘴里一溜板牙,单看这种形象就有点反人类,唤作“黑煞”再贴切不过。他从小学武,到处打人,让远近的乡邻人见人怕,后来又配上刀枪,有了同伙,更成了比传说中的“悍妖”还吓人的狠角色。“黑煞”本是人,竟比妖怪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足见其“恶力”有多强,破坏性有多大。
那么这种为害一方的乡里一霸,究竟是什么货色呢?“他什么都不是,他是坏人的头儿。只要干狠事坏事就得找他。他打人的时候要站到一个凳子上,专打人的脸,捣人的肚子。他用皮带抽人,能一口气把人抽昏过去。被他打过的人,就再也活不久。”原来,嚣张跋扈的“黑煞”既不是官老爷也不是小衙役,充其量只是一个为虎作伥的“临时工”。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临时工”,却总能把那点临时的“权力”无限放大,总能抓住一点点临时的“好处”把坏事做绝。所以他想得到小獾胡就能判它死刑,看外祖母不顺眼就能命她立正,碰到父亲回家就能关他小黑屋,得到上边的“杀狗令”更能掀起一场人神共愤的大屠杀。并且,“黑煞”这样的临时工从来都是不折不扣的好奴才,他们最懂得该向谁立正、该让谁立正,他们的恶从来都是针对无助的弱者,甚至是无辜的小动物。比如那个愿为“花虎”提供庇护的林场副场长郑撸子,“黑煞”就不敢招惹,他很清楚自己是什么玩意儿。无怪乎父亲说他“就是最残忍、最卑鄙、最胆小的恶魔!”面对这样的恶魔“黑煞”,手无寸铁且背时背运的人们只能自求多福,免得被他盯上、撞上、算计上,只有年少气盛的“我”义愤难平:“如果自己有一支枪,在林子里遇到‘黑煞’,真的会跟他开火。”
当然这只是一个少年的英雄梦,且不说他手无寸铁,就算他真的拥有一支枪,真的朝“黑煞”开火,大概也无法消灭它。要知道,“黑煞”从来就不是一个人,它是传说中的不明物体,又是一种不断更新换代的“恶力”。不是吗,生活中总不缺少好话说尽的“叼盘侠”,也不缺少假为民除害造福子孙之名做出的万恶之行。比如瘟疫期间再度爆出的“杀狗令”,哪一个狗杀手不是正义的化身?可悲的是总是有人发布“杀狗令”,总是有人活在“杀狗令”的迷狂中,一有风吹草动,便会戴上红袖章,举起大喇叭,甚至挥起大棒,把一切不顺眼的东西统统消灭。如此种种也就不难理解“我”的恐惧:“时过而境未迁,“黑煞”他们原来还在,他们竟然就活在近邻。”这句话近乎直白,作者显然是想告诉我们“黑煞”的大行其道,对付这等“恶力”,一支枪显然不够,爱和恨显然也不够,我们能够做到的,首先只能是不要被“黑煞”撞上,更不要成为“黑煞”的帮凶。
5
在很大程度上,我愿意把《爱的川流不息》看作张炜的自叙传。不光是曾亲耳听过他满怀深情地讲述那些动物朋友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里毫无保留地坦示了个人的脆弱、微小和恐惧,他在对异类生灵战战兢兢的爱中表达了一种卑微的自尊,也在与小獾胡、融融的相互驯化中传达了一种跨越族类的脉脉温情。同时,这部作品既立足于当下,又续接了他自芦清河时期创设的叙事语境,和《古船》《梦中苦辩》《蘑菇七种》《九月寓言》《它们》《你在高原》《半岛哈里哈气》《你的原野盛宴》等作品建立了千丝万缕的互文关系,看到海边丛林、林中小屋、葡萄园、渔铺、大李子树、黛色的南山,以及外祖母、采药人老广、小伙伴壮壮、郑橹子等人物,熟悉他作品的读者多少会联想到更多的相关信息,也会和他的动物朋友亲如故人。张炜通过这部小说再次重获童年,我们由此收获一个异质的世界。
所以,有融融的作家是有福的,他汇聚了“爱的川流不息”。认得融融的读者是有福的,他认出了一个大骨骼的人,他爱这有猫陪伴的人间。
(本文发于《十月》杂志2021年第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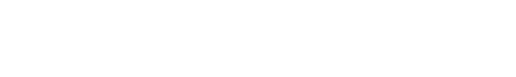
 您现在的位置:
您现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