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顺馨的《1962:夹缝中的生存》谈起
历史既具有波澜壮阔的一面,也必然具有其平淡日常之处,但对于注目历史的人来说,却往往喜欢注意前者,因为这好像更能体现出历史的精彩,但历史并非总是精彩的,尤其是当我们去了解这精彩的原因的时候,那种宿命的平淡可能却正是精彩的成因。正如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里说的:“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上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而1962年,对于当代的文学历史发展而言,也正是与此相类似的年代。
相对与1966年开始的惊心动魄,相对于1957年的你死我活,相对于1978年的改革大潮,1962无论从政治、历史还是文学来看,的确显得平静了许多,严峻的阶级斗争似乎有些平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也似乎使知识分子有的安定的感觉,于是,历史好像真的开始了它的休养生息时代,而作为“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中的一本的陈顺馨的《1962:夹缝中的生存》,所叙述的就是这个时代中的中国文学的存在境况。
虽然对于知识分子作家们来讲,处于一种外在或内在的矛盾夹缝中是一个生活的常态,但1962年前后对于当代的作家或理论家来说,这种不尴与不尬却显得尤为突出。在阶级斗争的大是大非面前、在政治上风云激荡中,知识分子反而能够较好地把握自己,站稳自己的立场,就像在“文革”中,知识分子的忏悔也是真诚的、痛切的,对自我的认识也是明确的。但是在1962这样一个政治形式并非很明朗的时代,他们却有些难以把握自己了,这样,此后在“文革”中的境况也就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了。陈顺馨的这本书对这种境况叙述的极为真切。这种境况在文坛的各个方面都有富于代表性的体现。
例如周扬,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经典阐释者,历次文艺斗争的执行者,在这个时期,却有些难以把握历史的脉搏了。一方面,他认识到了建国后文艺路线中的“左”的危害,试图进行反思和一等程度上的纠正;而另一方面,他又无法从根本上说清楚(或者不原说清楚)这种危害的根源。就像陈顺馨分析的那样:“周扬并没有否定政治对于文艺和其他方面的‘统帅’或‘灵魂’作用,他所担心的是,政治如果从一条牵动兵将或肉体的‘红线’变成一块‘红布’(过多或过宽)时,它不仅遮盖了兵将的毛病或肉体的缺点,还遮蔽了可以补救这些毛病或缺点的可能性,更严重的是把自己的作用也消解掉了。”其实对于周扬来讲,他未尝不知道文艺疲软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但他所处的地位使他的使命是维护而不是质疑这种文艺路线,因此他的尴尬也就在于一方面要补救,另一方面又知道补救是于事无补的。而且周扬也能够察觉到,即使这种补救也并非一定能够被主导意识形态所认可,所以他阐述这些观点,都是以讲话、报告的形式而不是以正式的文件、文章的形式出现的。就像陈顺馨统计的,在1961和1962这两年间,周扬在各界人士和各地所做的讲话就占《周扬文集》这两年文章总数的80%,而且大多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这也正说明周扬的顾忌之深和对自己努力的缺乏信心。这也正是他的尴尬之处。
再比如当时非常兴盛的杂文和引人注目的杂文作家们,也同样处于这种夹缝之中。以邓拓等人为代表的杂文作家们,以一种弥合现代“杂文”和“小品文”的一种新知识性杂文的形式,为时代的空虚提供了精神食粮。因此像“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长短录”之类的报刊杂文专栏大受欢迎。可是像邓拓依然能够感受到时局的变换,无法放手的去创作。就像陈顺馨分析的那样:“可能由于两个既定的身份,他们注定‘野’不起来。一是政治身份;他们身处权力中心,忠心于党的事业,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的磨练后,容易变的谨慎、老练与世故,这也是他们的生存之道。二是文化身份:他们虽有‘书生’或学者的‘骨气’,却缺乏挑战权威的胆量。夹在严峻的现实和这两重身份之间,他们的杂文虽不可能成为香甜的百合花,但也不会是‘野百合花’。邓拓、吴晗和廖沫沙这杂文‘三家’,只能选择以历史知识作为‘武器’来面对现实,这是建制内的知识分子所处的‘夹缝’状态的一种写照。”
还有像是当时的戏剧创作,虽然在毛那里,戏剧成了各种文艺形式中最重要表现形式,但在“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提倡下,历史剧的兴盛却无法掩盖剧作家们的那种左右为难。一方面,剧作家不愿把戏剧仅仅当作现实政治斗争的武器,而另一方面,现实的政治斗争又要求他们通过创作来演绎现实。于是,他们也同样的处于了“历史”、“现实”与“政治”的夹缝之中。就像曹禺,在这个时期创作的《胆剑篇》和《王昭君》,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了配合形式的痕迹。
同样象是60年代蓬勃起来的散文诗歌创作,也是如此,陈顺馨在叙述这个抒情的时代时,用了这样一句很形象的话作为章节的副标题:“困难时期的挚情、闲情、矫情与激情”,这的确很值得人回味,虽然对于创作来讲,有各种情感包含在里面是正常的,可惜在这样一个年代,作家却难以抒发自己的真情。本来的闲情中可能必须人为的加入激情,本来的激情可能最终又变成了矫情,本来的矫情可能却被认为成了挚情,最终都开始向滥情转化。比如老舍在描写内蒙古的林海、草原、渔场和各风景区的时候,突然生硬地蹦出了“人民公社万岁,万万岁!”等口号,并配合政策路线的“我们是在每一新建设与新事物中都可以看到三面红旗的光辉!是,内蒙的辉煌成就便是遵循总路线的必然结果”等句子。像杨朔,虽然诗意和对散文的探索使他的创作独树一帜,但浪漫主义的抒情最终却总是首尾于现实政策的赞歌上,豪情立时变成了矫情,让人惋惜。而郭小川的《望星空》和《甘蔗林――青纱帐》两首诗,正是在这个夹缝中的时期的状态的最好写照,正如陈顺馨说的:“郭小川的作品虽然仍然以抽象化的‘革命’来承载他的感情,但具体的个人记忆与生死经历,以至处身的环境,让他‘无可救药’的革命乐观主义中,保留了一份真挚和纯洁的激情,也在‘消肿’的过程中拾回一份现实感。”看来,在一个历史需要抒情的时代里,作家要抒发自己的真情却又是很困难的。
可见,虽然1962是一个调整的时期,虽然文坛出现了一种春天的征兆,但无论是对小说、戏剧还是散文创作来讲,真正的兴盛并没有到来,对于作家们来说,刚刚经历的政治风浪已经使他们的嗅觉更灵敏了起来,无论是抒情言志还是载道也同样的谨慎小心,他们总是“欲说还羞”、“犹抱琵琶半遮面”,如果“偶尔露峥嵘”的话,那等待他们的将是1966的更大的政治风云。而陈顺馨的《1962:夹缝中的生存》就为我们描画了这样的年代里的尴尬的文坛境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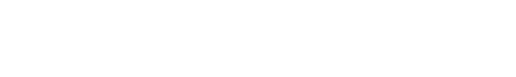
 您现在的位置:
您现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