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叙事纷然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中,现代中国的历史实践、文化建构以及国人基于各自不同的现代想象所传达的现实经验与精神意绪一直是众多阐释者的一个释义焦点。其中,文学研究特别是有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解读与辨析更是成为一个持久的线索。可以说,学界在相继经历了“思想解放”时代浮躁的价值评判和其后“学术规范”诉求中的价值困惑之后,重又接续了文学与历史相关性的思考。文学的生成与变异本来即是历史演化中最繁复敏感的一根神经,而中国现代文学又身处颓败与新生的历史关节点,所以格外强化了其可阐释性。然而,新一轮重叙历史的冲动也面临诸多新的言说困境,在走出了单一自明的启蒙神话之后,新的话语资源(无论来自经典的学术史传统抑或崭新的西学理路)一方面带来学术新知,同时也在时时形成新的迷思。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解洪祥教授的新著《中国现代文学精神》(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通过对新文学精神谱系的细致梳理和深在把握,不仅重新厘定了现代文学的精神传统,而且自觉关联中西历史演进中的现代性规划及其实践,有力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精神”这样一个富有思想厚度和学术强度的论题,显示出文学研究在当下新旧困扰中寻求有效突破的实绩。
作为新潮涌动中释义活动的一个重要的阐释对象,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相关的历史文化语义被人们不断地重新命名和反复言说。实际上,这种命名和重叙文学史的冲动首先需要处理的是如何设定一个有效的论域——不仅是文学史断限所带来的时段划分问题,而且要确立论者自身的研究范式以及在怎样的阐释语境中面对对象。对《中国现代文学精神》而言,著者不仅对论域的设定有充分的自觉,而且的确将研究对象置于一个相当宏阔的历史与文化视野中展开论说,可以说,这一视野既意味着时空意义上的延展和阔大,同时更显示出著者思想触角的伸展和文学史观的深广度。正如著者所说:“本书自觉站在中国社会历史第三次大变动的历史高度和时代视角回看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历史生成和演进轨迹”,这一研究视界的确立使著者对现代中国文学精神的论说获得了双重的历史参照——一方面将现代文学置于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继而向新型政治理念规划下的历史新时代的转型进程中,同时又将对象所身处的中西历史文化演进的相关性贯穿始终。这样,现代文学精神作为中国社会自身演变中的一个历史环节与文化链条,与传统中国历史文化意识复杂的夹缠关系得到辨析和呈现;同时,这种辨识又是在中西近现代史的历史文化变革背景中完成的。值得指出的是,著者提出并自觉实践着的“中国社会第三次大变动”这一解释模式蕴含了现代文学研究不断克服学科自身困惑的又一新的可能性。在著者看来,发端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历史新一轮的转型实践延续至今,正是一次尚在进行之中的社会历史大变革,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中,其深远的历史意义正如同中国历史上既有的两次大变动(秦汉模式的确立和“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引发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新中国政治实践的完成)。对现代文学研究而言,三次历史变革尤其是后两次历史变动所带来的阐释资源是复杂厚重的,而如何廓清历史变局带给文学研究的新语境,从而有效地利用历史资源、走出种种历史与观念的误区、步入历史研究的某种新进境,这正是著者反复关注并努力化为研究实践的一个重心。“站在中国社会历史第三次大变动的立场看问题,和站在第二次大变动的立场看问题是不完全相同的。”后者往往只能看到历史方案的高歌猛进,而前者则引发出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实践与文化建构的深度发思。与此相关,“十七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基本是站在第二次大变革的立场上的研究,特点在于着重从政治方面、从现代革命的成功实践方面做出充分肯定。由于取向的单一和狭隘化,这种研究存在严重弊端。新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主要是站在第三次大变动的立场,在突破十七年模式、展开多元立体化研究的同时,又将政治视为文学研究的异质成分加以淡化和排拒。”显然,狭隘的政治视角与单一的文化启蒙思路都无力有效地解释现代文学精神的真正内涵,第三次社会历史大变动本身其实已经足够地凸显出现代性历史实践与文化建构的复杂关联,因此这一时代视角所带来的理应是真正直面和解释历史发展与文学演化的相关性,努力寻找中国现代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现代性历史实践、文化规划与文学想象之间的内在联系。
研究论域的自觉延展其实正来自著者“问题意识”的强化,既往的种种解释模式尽管在言说立场上不断做出调整,但要么规避历史主流自身的“潜流与漩涡”,要么索性取消文学对象的历史实践品格,或者以一种未经辨明的现代理念取代以往同样缺乏反省的单一政治立场,凡此种种其实都泄漏出对研究对象所关联的诸多层面的“现代”问题未能自觉构筑问题视野和反思意识这一解释困境。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学所遭遇的一系列文学内外的困扰无不最终指向百年中国近现代史转型的一个核心母题——“中国社会的历史与意识危机”。可以说包括文学实践在内的现代中国历史进程已经对此做出回应。作为历史阐释者,不仅应该捕捉和印证这一“中国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更要细致勾画历史实践与精神演变的具体轨迹,有效解释历史究竟怎样、何以如此以及未曾实现的可能性。正是在这种自觉强化的“问题意识”烛照下,著者对一个长期被研究者曲解、忽略或简单拒斥的历史与精神线索——马克思主义引领下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潮及其历史文化实践做出了相当深刻的反思。近年来一些清醒的文学史家重又提起当年王瑶先生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范式的一种质疑:“你们讲二十世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或只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文学的影响?”的确,离开对中国现代主流文化与政治意识及其实践的索解,我们根本无法说明包括中国现代文学精神在内的种种“中国问题”。值得欣喜的是,在本书中著者所设立的阐释目标正是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精神历史生成与演化的分析,提出对中国现代革命与社会主义实践的一种解释。反之,也正是由于直面主流政治实践和文化建构,著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解释才有可能是有效和完整的。书中提出的三个富有创见的学术命题尤其值得关注:“背离与遗忘——马克思主义积极扬弃论和辩证个体观”、“失衡与悖反——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以及“人本与民本——中西文学及历史现代转型比较”。由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情境中一度发生的畸变与步入歧途、革命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这两大精神传统各自在政治实践与思想启蒙、现实选择与文化创造当中的相互冲突特别是内部失衡与自我悖反,以及二十世纪人类现代性实践的两大指向各自历史命运的观照,都在书中得到一种有效的阐释。一些未经彰显的精神线索和悬而未决的精神与历史症结——如基于二元文化和两类觉醒的五四新传统、丁玲胡风的个体主体性之于延安文学精神新整合的结构意义、消解个体性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种种表现等等,也都成为著者致力发掘和勘察的对象。在此意义上,本书的确重新绘出了一幅现代中国文学精神的地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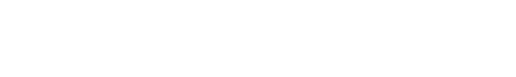
 您现在的位置:
您现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