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守本与开新:阎锡山与山西教育》有感
美国当代历史学家盖伊(Gay, P.)指出:“没有分析的历史叙事是陈腐的,没有叙事的分析是不完善的。”这是新叙事史的代表性观点,亦可视为西方史学在或偏于叙事与或偏于分析之间长期博弈的理性归结。在历史研究中,永远都不能抛弃以事实为基础的叙事,同时,支离破碎的历史碎片惟有经由史家的分析才能接近历史的原生态。那么,衡量一份史学作品,其焦点就落在了叙事与分析的维度之上,也正是不同的史学研究者有不同的叙事风格与分析技艺,才使得历史生活的复杂面相经过一代代史学工作者的雕琢而渐渐清晰。中国教育史研究始终注重借鉴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为学科建设服务。尤其在传统史学日益满足不了当代中国教育史发展需要的时候,如何从新史学中汲取营养,使教育史学科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已成为学界同仁共同努力的方向。华中师范大学申国昌教授撰写的《守本与开新——阎锡山与山西教育》(以下简称《阎锡山与山西教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是西方当代新叙事史学导引下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先放之花,也是学界对阎锡山的非主流教育理念和办学实践的首度系统研究。该著对于教育史研究如何运用史学最新理论成果、拓展教育史研究领域、转换研究范式作了创造性的尝试,尤其是在叙事与分析的二元处理上,有独到之处:
首先,叙事与分析相融。作为教育史学研究成果,《阎锡山与山西教育》对传统史学编纂体例有所突破,采用了现代叙事史学风格呈现教育历史的文本,表现为结构的整体性、内容的推理性、行文的流畅性和语言的通俗性,这为阅读、理解该著增加了美学的韵味。著者坚守论从史出、叙事有据的史学本色,注重历史写作的美学性的同时,将史学叙事与文学叙事明确区分开来,即将叙事建立在事实分析而非浪漫想象之上。新叙事史下的叙事已经不同于传统史学叙事,即叙事与分析的紧密相融。《阎锡山与山西教育》通篇运用史论交织的叙事性语言开启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即用现代的手法重现了民国时期山西教育的历史画卷,发现了一名军阀的另类面。通览《阎锡山与山西教育》发现,阎锡山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体现在国民教育、人才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等诸多领域,俨然就是一位前沿的教育践行者,其实这是著者的分析结果,在对史料爬梳基础上,著者提炼出了阎锡山“以国民教育培育根基,以人才教育铸就精英,以职业教育谋求生计,以社会教育感化民众”的系统教育观。而在分析军阀办教育这一特殊现象时,著者采用的理论基础是政治社会学理论,超越了单纯就教育论教育的狭窄视野,赋予了更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现实观照,展现了教育与社会体系当中其它子系统之间的亲密关系。著者始终抓住阎锡山首先是作为一名“政治人”而非“教育者”的身份展开分析,这就在充分肯定其客观的教育成效的同时,又使军阀办教育实质上为其政治统治服务的本质,在历史的审判席上一览无遗。同时,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阎锡山与山西教育》既尊重了阎锡山苦心经营山西教育的史实,又未因此而粉饰其军阀统治的本性。
其次,事实与感觉协奏。新叙事史的要旨之一在于其在叙事的同时,亦注重理论分析。《阎锡山与山西教育》不仅重视理论分析,而且是有感觉地分析。在史学研究中谈“感觉”,似乎存在这样的“危险”:在科学至上、规范宰制的学术生态中,凭“感觉”焉能演绎历史?而杨念群教授曾指出:“中国史学需要一种‘感觉主义’”,“如果不从‘感觉’的角度去深究历史生活的复杂面相,往往使我们对一些历史场景所表现出的真实性做出完全相反的错误判断”。通读《阎锡山与山西教育》之前,很难将阎锡山这位坐镇一方的军阀与关乎国计民生的教育联系起来,即便是身为山西人的著者亦言“‘阎锡山’这个名字从小就以反面人物之典型深印心间”。在教育史学研究领域,阎锡山的教育研究是非主流的,是被搁置抑或是无人敢涉足的领域。那么,做这样的一种研究,似乎存在又一重“危险”:能否客观真实地叙事?《阎锡山与山西教育》通过事实与感觉的协奏保障了历史叙事的客观性,即著者穿越线性教育史研究思维的藩篱,转换进化论式的研究范式,用“感觉”架构起“问题意识”。教育史研究中长期存在这样一种思维:人类社会的教育遵从低级到高级、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轨迹。进而导致这样一种研究范式的形成:教育史学研究课题的选择往往从教育现实出发,去历史中寻根,描述研究对象在一个时段内的产生、发展、成熟、更新的教育进化史。这种进化论式的研究范式规约下的教育史研究视线必然指向上层、中央、主流、精英的教育思想,而底层、地方、非主流、大众的教育活动是被忽略的。《阎锡山与山西教育》的“问题意识”集中体现在其对于“军阀办教育”这个特殊现象的发现,在掌握丰富的历史素材的基础上,打破对阎锡山作为军阀必然施行反动统治的刻板印象,运用基于事实的想象重回历史的现场,分析了这位守治一方的军阀如何利用教育为自己的政治统治服务。显然,《阎锡山与山西教育》实现了教育史研究范式的转换,即从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向教育活动史转换。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但也是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行为,而唯科学主义学科发展思维借思想、制度之名使教育史研究虽“居庙堂之高”,实“处江湖之远”,这是教育史学走入困境的原因所在。相比同时代的教育学者、精英来说,阎锡山的教育思想谈不上系统、科学,他在山西的教育所为也是游离在国家教育制度之外的,然而,他的教育活动却是真实存在的,实实在在地促进了山西人与社会的发展。著者正是基于这种感觉架构起问题意识,同时具有对史料细微之处敏感把握、驾驭的能力,才从复杂的历史面相中淘沥出一段鲜活的基层教育史。至此,可以感受到,著者这种以问题意识为范导、以政治社会学理论为基础的历史诠释路径所具有的史学解释力度。
再次,传统与现代并用。“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无休止的对话”,《阎锡山与山西教育》除了具有叙事与分析的解释学范式之外,还确立了传统与现代并用的史学研究方法论。其一,史料分析法的运用。“没有史料的教育史研究好似无米之炊”,著者首先强调史料的重要性,其次确认与研究相关的史料、分类之后逐步收集与摘录,最后对于伪史或美化过的史料实施甄选。在保证真实的史料的前提下,著者为该研究收集到等身的第一手资料,包括64种近代的档案、资料;17种近代创办的报纸、期刊;117本中外专著。其二,计量史学的运用。为直观地展示阎锡山主政下山西教育发展的概况,以及为叙事的真实性提供实证性的数据,著者运用了计量史学的方法,将民国时期山西教育发展的各种数据作了统计分析,形成图表达62张。其中有纵向的山西省历年教育发展概况,亦有横向的同期全国教育发展水平的比较,使该著所研究的对象在叙事时更加直观、精确与科学。但著者并未走向某些史家宣称“不是计量的历史学就不是科学的历史学”的极端,在《阎锡山与山西教育》中,数字分析只是一种辅助方法,主导方法依然是文字分析。其三,心态史学的运用。菲利普?阿里埃斯(Philippe Ariès)在《心态史学》中解释法王法兰西斯一世在与情妇幽会后回城堡的路上被一所教堂晨祷钟声吸引而前往教堂虔诚地向上帝祷告的行为时称,国王对情欲和祈祷的态度同样出自本能,而并不仅仅将其祷告的行为归因为钟声所引发的忏悔之举,这就是心态史学与传统史学在解释上的区别所在。阎锡山作为一名军阀,他对共产党、人民群众的镇压与热情兴学以强晋富民同样出自于本能,二者之间并不存在道德上的二元背反,均是权力欲下的正常表现。所以,借助心态分析,阎锡山兴办山西教育的动机出于对功利性、虚荣性的追求,同时又受着浓重的乡土情感、尊儒重教的个人喜好的驱使。总之,传统与现代史学方法的共同运用,为叙事与分析的客观性提供了方法论依据。
经典音乐的演绎除了有优质的乐器之外,最主要依靠演奏者敏锐的瞬间捕捉乐感的能力。历史研究也是如此,史料可视为乐器,史学家需要有音乐家般的感觉力,唯有事实与感觉的完美协奏才能有优秀的史学作品问世。《阎锡山与山西教育》成功演绎了“地方军阀办教育”这一特殊的教育现象,堪称一部叙事与分析相融、事实与感觉协奏、传统与现代并用的范式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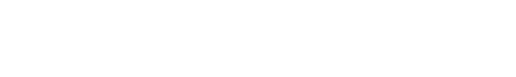
 您现在的位置:
您现在的位置: